从上海闲话中看上海男人
时讯
留在上海话语词中的各种上海人的特点已经成为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和优良传统,同时也构成了以商业为基础的、与农业文化不同的海派文化的底蕴。

上海话中有些词语也记下了上海男人的形象。上海男人在繁忙的处世办事中除了上面说到的养成了“精明活络”的内质外,从外表来看还有“落落大方”的绅士风度的一面,讲究“派头”和“气质”,“坐得正,立得稳”,心胸开阔,襟怀坦白,不在小事上斤斤计较。遇到一些朋友或同事为难的事,常常一句很轻松的话:
“小开司(case,小事一桩)”
“噢,小开司,交拨我办好了。”
帮忙解决问题,看成是“毛毛雨,小意思”,“小菜一碟(小意思,很容易)”,不足挂齿。
上海的白领先生,过去有两种出身,一是从“学徒”磨起的“苦出身”,另一种是留洋回来的富家子弟,他们讲究“裤缝笔挺,皮鞋锃亮”,还有“头子活络,卖相登样”,过“风风光光”的“写字间”生涯。有许多的城市,也有工厂老板,也有的是劳苦大众,但是它们不能发展成为一度是世界商业金融中心的大都会,就是缺乏这样的一大群上海男人。
上海“老克拉”

图为盛宣怀家族后代盛毓楠老年照
上海的大男人中,存在着这样一个重要的“白领”阶层,为上海商业化经济的支柱。他们讲究仪态,举止温文,一副“知书达理”的样子,多有个人业余爱好,充满好奇和憧憬,具有创造力和能耐力,过着明快炽热的生活,“有台型”,往往是一种细腻而富有风情的形象。尤其是那些见多识广倾情西方文化、有国际视野的人,给人的感觉温馨而又“洋派”,“交关克拉”。更有资深甚者,被称为“老克拉”。
上海话“老克拉”一词,与海派经济和文化直接有关,探索其源,“克拉”来自英语“carat”,是宝石的重量单位,一克拉等于200毫克。在过去的珠宝店里,司务们遇到三克拉以上成色的钻石宝戒,常常会把大拇指一翘,称一声“老克拉”。后来用它主要喻指那些从国外归来见过世面的、有现代意识的、有西方文化学识背景有绅士风范的“老白领”。

再接着,从他们的文化追求和生活方式着眼,又延伸了从英语“colour”(彩色)和“classics”(经典)来的特色含义。这个阶层收入高,消费也较前卫,讲究服饰和休闲的摩登,在休闲方式上也领潮流之先,精通上海中西融合的时尚和社会,追潮恰如其分。
今又扩指到遇事在行、处世老练、有生活经验、有绅士风度的年长者,他们信口说来,都是典故。如:
“我想跟大家介绍,搿两位上海滩浪个老克拉,上海三四十年代个事体,可以问问伊拉。”

在全民都穿中山装的年代,“老克拉”却穿出西装,在大家普唱革命歌时候,他解不掉老习惯去“打落弹”和“跳蓬拆拆”,搞“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因为逆潮而动,一时“老克拉”便成为贬义词。不过“六十年风水轮流转”,上海又走在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前哨了,如今“老克拉”又开始“吃香”了,上海精通中外时尚的白领又在壮大起来。他们和有些“老板”一样是成功男士,被有些人誉作是“积优股”和“潜力股”。
上海男人会“做人家”

即使在外是个“大户”,在家还是交关“做人家”,“一块洋钿掰两半用。”这恰恰是上海男人理性理财的优点。他们主张“自靠自”的自力更生,“爷有娘有勿如自有,家主婆有还要房门口守”,他们不啃老,不仰人鼻息,也不盲目“掼派头”,装大自吹地“摆奎劲”,同时处事也实事求是,“勿摆丹老”使人上当。
那时上海在每个大型的工厂车间里,都有一些技艺精致、老练一流、会解决各种生产上疑难杂症的老工人老技师,他们的工作作风十分严谨踏实,上海话里称他们为“老法师”、“老家生”,他们是上海工厂的“宝贵财富”,有力地支撑着上海的工业产品的高质品牌。上海的“老板”在解放前也是敢于与外国老板平起平坐“别苗头”苦“打世界”的一群。

上海更多的男人属于普通市民阶层。他们有个特点是十分“顾家”,大多人可以临时或长期担任“马大嫂(买汏烧,意为家务活)”,屋内小修小补,是样样“来三”的“三脚猫”,被戏称为“家庭妇男”。对老婆也是“一帖药”,甚至怕老婆,把老婆供为“玉皇大帝”,言听计从。
上海话中的“花头经透”、“花露水足”往往不用在“资深美女”“熟女”上,而是“资深男人”的法宝,他们对老婆“有花功”,所谓“软硬功夫”都会,温柔体贴,乐于做“居家好男人”。有的人虽胸襟不够开阔,但多数不“拆烂污”,不夸夸其谈“牛屄吹来野豁豁”,“侃”这个词在上海话词典中没有同义词。但他们要面子,要“扎台型”,与别人“别苗头”,不能“退招势”,就是“吃泡饭”也要“着西装”,要“卖相”,“上台面”,注意自己的“身价”不能丢,过去有一个词叫“洋装瘪三”,说的就是即使“穷得溚溚渧”,外出一套“洋装”还是必备的。不管是谁,对“上只角”社区的情调和氛围是普遍认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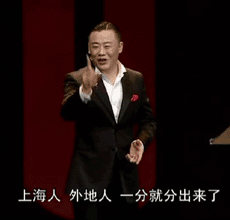
“相骂”勿“相打”
上海大男人的特点是心胸开阔,目光前卫,工作勤奋,守信用讲规则,这是与这个海派都市海纳百川的胸襟和“上海速度”相和谐的。与“上海大男人”相对的观念是“上海小男人”,往往指那些缺乏气概的、精于小事、目光短浅的那些上海男人。

由于有段时期长期经济收入偏低,居住和伸展空间狭小,使一些上海男人变成了缺少气慨的、精于小事、又斤斤计较的“上海小男人”,过去乘公共汽车“吊车”、“逃票”,做做“黄牛生意”,到现在请女朋友坐“差头”眼睛还在盯着计价器上上升中的数字的。上海话贬之为“小儿科”、“小气”、“小手小脚”、“小家败气”、“勒杀吊死”,严重的叫他“一毛勿拔的铁公鸡”,为些小事争得“面红赤颈”。譬如,在电车上某甲一不小心踩到了某乙,有的上海人很少说对不起。
乙会说:“啊唷滑,出门不带眼乌珠的吗?”
甲说:“你脚上生了眼睛,怎么看见我的脚踏上来不避开呢?”
乙说:“踏痛了人的脚,还讲横浜理,真真碰得着!”(言下藏着“侬个出老!”)
甲说:“碰得着那能?碰得着那能?我同侬碰碰看末哉!”(等待着对方“吃瘪”)
这段对话选自汪仲贤的《上海俗语图说》,这种景象直到80年代初期还觉得如在目前,读来依然典型不乏韵味。

不过上海男人一般有自制力和一定的文明素养,“动嘴勿动手”,以使人“吃瘪”为界,这种边吵架边调侃的詈语在一些外地人看来,不知是相骂还是相趣。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推荐视频

剑网行动举报电话:12318(市文化执法总队)、021-64334547(市版权局)
Copyright © 2016 Kankanews.com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看东方(上海)传媒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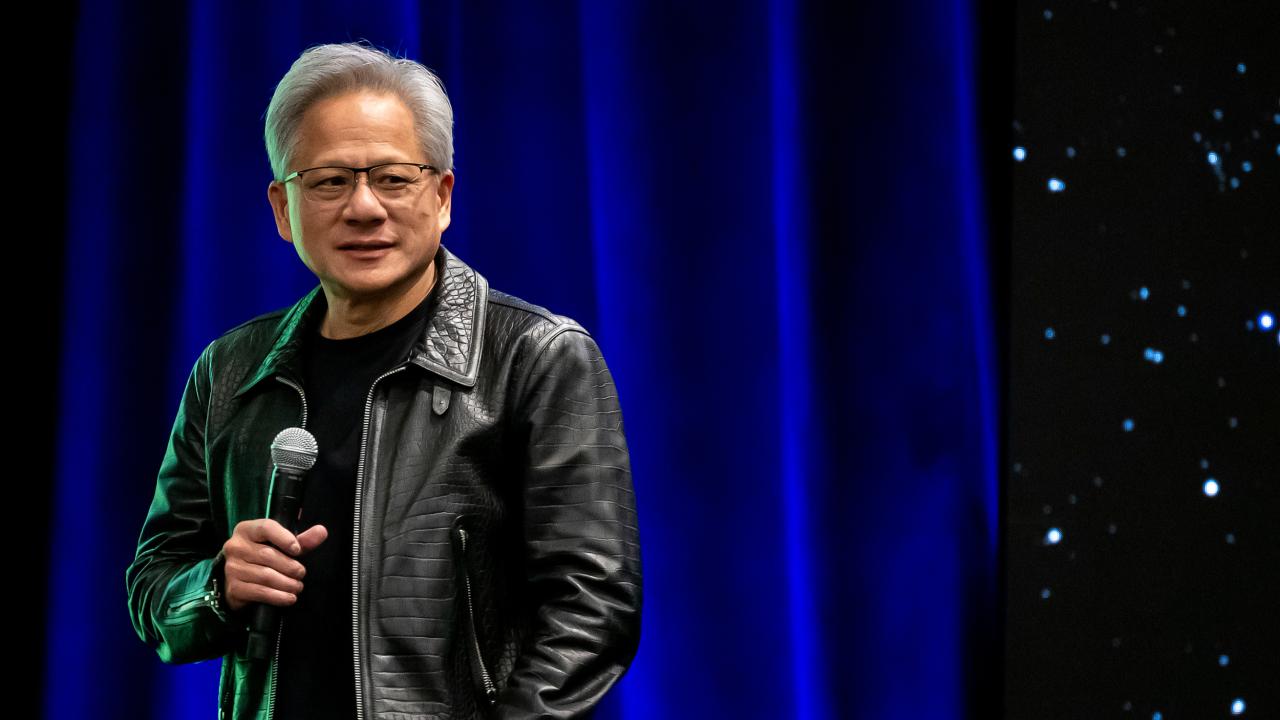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1114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111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