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内:每一个作家的过往是沉默的
时讯

路内
路内:本名商俊伟,1973年生,苏州人。从19岁起,路内就在苏州、上海、重庆的工厂里辗转,“失业、找工作、失业、找工作。”,他口中的工作包括钳工,维修电工,值班电工,操作工,仓库管理员,营业员,会计,小职员,电脑设计,小贩,播音员,摄像师,广告公司文案,公关公司老板等等。
2007年《收获》杂志在半年内连续发了路内的两部小说《少年巴比伦》和《追随她的旅程》,从此显露文坛。今年年初出版的长篇小说《慈悲》更令路内的写作广受关注,更被评价为最好的七零后小说家之一。小说家、上海作协副主席孙甘露在2016年5月20日小说《慈悲》的研讨会上说:“以前我有一种幻觉,好像路内是一个后辈,现在我觉得路内是一个我们要学习的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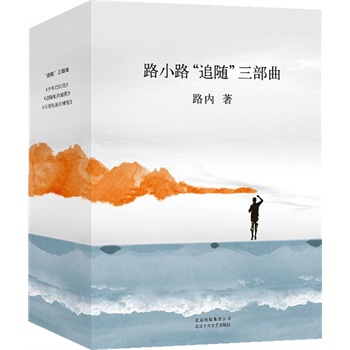
路内 追随三部曲
7月3日,茅盾文学新人奖的颁奖典礼在茅盾先生的故乡浙江桐乡举行。路内在前往桐乡领奖之前接受了看看新闻KNEWS记者的独家专访。
(Q:看看新闻Knews记者 A:路内)
Q:曾经看过一些媒体报道,在提及您的创作所涉及的题材时,引用一些评论家的话来说,就是大家都很好奇您为什么会对工厂生活那么熟悉。而就“从工人到作家”来说描述您,短短几个字就很有故事性。
A:每一个作家的过往是沉默的,讲出来对于作品没有任何意义。 在讲自己事情的时候,实话实说,真得是为了宣传。因为小说里面已经写了,不可能再登一遍吧。你让我讲文学理念,在媒体上没人看。讲故事的话,大家就都能看明白。慢慢地,你就会发现这是损害一个严肃小说作家的想法的。
这样的做法会有巨大的误解,呈现出对于作家的巨大曲解。这样的曲解存在于读者之中,存在于评论界之中——必须指出,它不一定是坏事。但它是一个现代性扭曲的东西,因为在过度媒体发达的时代,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文学本身是一个用文字构建的世界,用故事构建的世界。当你再施之以故事去注释它,这就有问题了,本身会产生悖论。
“从工人到作家”,它不仅是有故事性,本身也极具欺骗性。它不存在这样一个逻辑:一个人从工人通过努力变成作家,或者一个人通过努力从农民变成作家。这里面存着两个问题:第一,他再努力也可能不会成为作家。文学是靠天分的;第二,不管你是什么出身,只要努力就能成为作家。通过努力你可以从任何人成为作家,这是成立的;有天分的人不用努力也可以成为作家,这也是成立的。唯独通过努力从什么什么成为作家这是不成立的,这本身是让文学庸俗化的说法,最后你励志的是一些畅销书作家。没有人谈论莎士比亚、荷马是有多努力,所有的严肃作家、诗人、写史诗的伟大作家看见这个都会觉得非常可笑。
狄更斯是从一个小学徒到作家的,但是谁会去讲他做小学徒的事情呢?大家不讨论这个问题,大家讨论狄更斯对那个时代的伦敦如何了解——从上层的伦敦社会到下层的贩夫走卒乞丐全都了解,那是他的文学资源。并不是狄更斯从一个小学徒做起,所以他才写出了《大卫·科波菲尔》 、《远大前程》, 那是因为他从那个阶层出身;但那个阶层像他那样了解伦敦的依然有无数人,只有他在文学上是这样写的;同一时代仍有很多作家在写,但是两百多年之后那个时代留下的作家却只有狄更斯,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伟大的文学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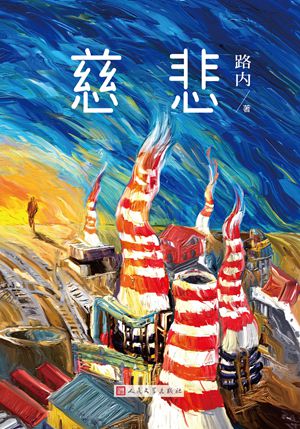
小说《慈悲》
Q:如果对于您过往的生活有所了解,再来看您的小说,读者往往会产生某种联想,比如路小路身上会不会有您的影子?
A:小说都是假的,编出来的。你说书中传达出来的精神是真的,但这是你的东西。这是作品和你之间产生的对接。对于作家的故事很多时候都是误读,并不存在一个真相的存在。作家的故事对接到他们自己,然后通过他们自己再到作品,这些作品和故事之间的距离其实非常遥远。你很难把三个角给对接起来,这个连连看是连不出来的。
故事性对作家没用,一部长篇小说就足够把自己的一生给写掉了。如果一个作家一定要说真实在文本中间占有什么位置,具有多少价值,那这个作家就是骗子,就想骗取一点廉价的名声而已。
Q:我们在读小说的时候,难免会作比较,觉得这个作家的小说风格很像某一位作家等等。您如何来看待创作模仿这个问题。
A:模仿是文学写作中免不了的,要看你模仿什么了。 有些模仿句子的写法,那叫练笔。 更深层次的是学习某位大师的精神气质,但这就不叫模仿了,那叫追随。追随一个大师往前走,就看你喜欢哪些人,是否符合你的气质。
作家卡夫卡、福克纳、狄更斯、海明威等等,都是被很多人所追随的,也包括被我追随。 这里面包含了对他们的模仿,但更多的是精神上佩服这个人。比如贝克特,我没有模仿过他,但我愿意追随他,因为他的精神气质非常符合我。
Q:您新出版的《慈悲》反响不错,但不少读者误以为它是一本畅销小说。好像在“畅销”这个问题上,有时候严肃小说、通俗小说和畅销小说会在读者理解中变得很模糊。
A:一部新的严肃小说要卖得好,是要经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同样是“畅销”,但本质上和畅销小说是不一样的。很多人看到一本国外的严肃小说在国内卖得很好,那是因为人家在国外积累了很长时间,在世界范围受到了认可,那个过程中受到的折磨是你所不知道的,然后到了中国好像是一下子火了。这其中是需要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酵,是一个被判断的过程。
并不是一个作家说自己是严肃作家,写出来的必然是严肃小说。严肃小说比通俗小说标准更苛刻。通俗小说只要故事合理漂亮,读者爱看,文笔还不错,有一些深度就可以了。而严肃文学面对的是一个无尽的深度,它不至于好看,但反过来说写得太难看的话,也会被人骂。

电影 《少年巴比伦》
Q:听说您现在在创作长篇小说的同时,还在从事电影剧本的创作。
A:一般来说手头上有这两件事已经足够了。写小说大体上为自己负责,写砸了连编辑都不能为你负责。我也不想天天躲在书房里写小说,时间久了会觉得无聊,写电影挺好的,需要去感知一下这个杂乱无章的工作是什么样子。
Q:电影创作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刚才您也提到了“杂乱无章”。
A:很多做纯文学的人受不了做电影,因为它太无聊,真的非常无聊。你做编剧的话,这不是你的作品,是导演的作品; 有时候你去做导演了,它仍然不是你的作品,是制片人的作品;你做了制片人了,它也不是你的作品,它是投资人的作品……你怎么写都不是你的东西,你还得把角色交给演员;演员演得不好的话,你也拿他没办法,因为挑演员是导演的责任……
一个电影投资再低也得一两百万,几千万的仍然需要编剧,上亿的话是不需要编剧了,只需要三维工程师就可以了。严肃文学创作就是一台电脑或者一张白纸,它只有这些东西,没有服化道(服装、化妆、道具),没有演员,没有导演,没有罗里吧嗦的制片人和一堆看剧本的外行——外行还可以诊断剧本提意见。
但是电影又是很有意思的,它从非常杂芜地走向单纯。好的电影都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东西,你会觉得背后什么都没有,然而最初却是在一个非常混乱的房间里进行的,惟其如此才会觉得稍为好玩一点。
推荐视频

剑网行动举报电话:12318(市文化执法总队)、021-64334547(市版权局)
Copyright © 2016 Kankanews.com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看东方(上海)传媒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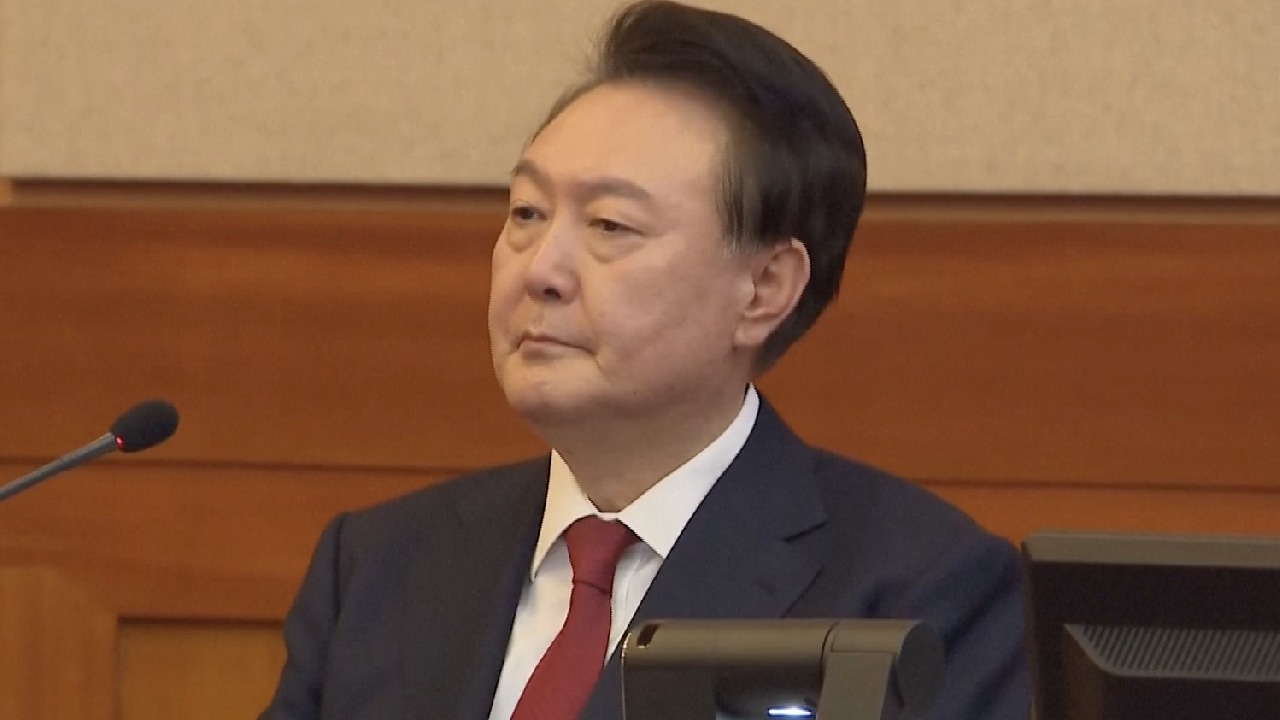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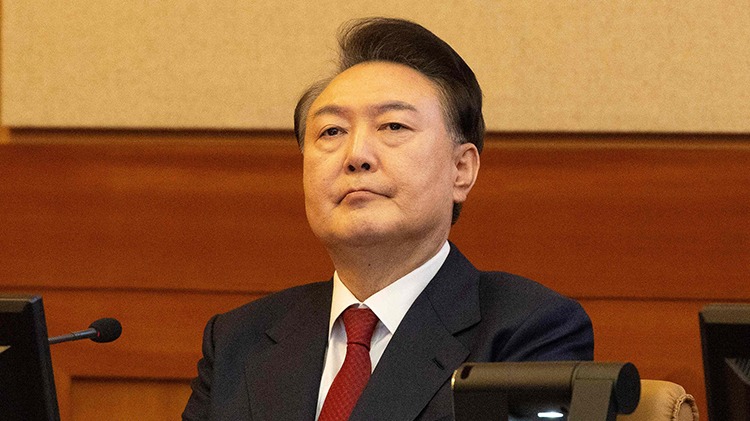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1114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111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