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孤岛”孩子:考上大学,却逃不脱艾滋歧视
时讯
今天是第30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我国公布的主题是“共担防艾责任,共享健康权利,共建健康中国”,旨在倡导艾滋病感染者享有平等获得健康服务的权利。平等的权利,是每一个感染者的渴望,也是一条依然漫长的路。今年6月,山西临汾红丝带学校的16名2017级高考生,在世人瞩目中走进一个专为他们设立的考场。随后,有15名进入高校求学。他们生活得怎么样?我们找到了他们。
一阵手机铃声打破了午后办公室的宁静。郭小平按键接听,那头传来焦急的声音:“郭伯伯,我去日内瓦,辅导员就是不准假!怎么办?”
“不要急,你慢慢说。”
“他不相信我能接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访问邀请,说这么好的事情怎么会落到一个刚上大一的学生身上,一定是传销组织骗术。”
那头不容插话:“按行程要求,17号必须办好签证,20号从北京出发。这样一搞,我担心来不及了。”
“别担心。我来解决。”
接下来给辅导员一通电话,郭小平觉得事情的确棘手——对方根本不相信一个学生突然被邀请去日内瓦这个事实,甚至怀疑郭本人就是传销组织头目。
辅导员最后撂下话:“要我准假,可以,拿手续和证明来!”问题是,这些所要求的手续和证明材料,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提供。郭小平顿时感到沮丧、焦躁,心情跌落谷底。
一
这个紧急的求助电话来自翠翠,一名今年才从临汾红丝带学校毕业而跨入大学的新生。她10月12日接到通知,10月20日至24日受邀在世界卫生组织日内瓦总部参观,并与总干事谭德赛交流。
她还将和同是大学新生的红丝带学校少年瑶瑶、涛涛、朋朋,一起与关晓彤、吴牧野等国内青年偶像艺人,在瑞士少女峰拍摄反艾滋病歧视的公益广告。
10月13日中午,翠翠找到辅导员提出请假要求,却遭到拒绝,对方还声称“坚持要去就退学”。翠翠只好将这个难题交给“郭伯伯”——郭小平,她最信任、最依赖的人,“当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时,我能想到的就是给他打电话,他是我最大的精神寄托。”
今年54岁的郭小平,我国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临汾红丝带学校的校长、创始人。13年来,他为39名因母婴传播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孩子们撑起一个家,为他们遮风挡雨。
“瘦弱的孩子需要关爱,这间病房改成的教室,是温暖的避难所。你用艰辛呵护孩子,也融化人心,你是风雨中张开羽翼的强者。”这是郭小平入选“感动中国”2016年度十大人物时,组委会授予他的颁奖词。
在这所特殊学校,孩子们心里从来没有“校长”概念,都叫他“郭伯伯”,实际上将他当成自己的父亲。郭小平在荧屏上眼泛泪光说:“他们就是我的孩子。现在我和孩子之间就是个‘情’字。”
“孩子”共有39个,其中16个今年夏天已高中毕业,是学校最早的一批孩子。其中,15个成功跨进了大学,翠翠、瑶瑶、涛涛、朋朋是其四。他们的这次日内瓦之行,是红丝带学校少年第一次走出国门。在郭小平看来,这是一件让孩子们开阔视野、并对未来发展极具影响的重大事件。

郭小平是红丝带学校这个大家庭的大家长。在孩子们心里,他就是父亲。
郭小平未曾料想到的是,他的电话也不能打消翠翠辅导员的顾虑。签证手续繁复,10月14、15日就是周末,时间尤显紧迫。有何良方破局?——必须拿出不可辩驳的理由让这位老师信服。
思前想后,郭小平当天下午第二次拨通辅导员电话,不得不向他揭开翠翠的特殊身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此次是受世卫组织邀请前往访问、交流。
这一下又让老师懵了。“他不相信我是感染者,跑来反复询问我,还想着要我怎么证明这个情况。后来要求让我爸爸到校给我办理假条,爸爸是农村人,很少出远门,找不到高铁站,也不会买票。”翠翠当时急得哭,“郭伯伯当时准备连夜赶过来。”
好在有了转机。郭小平梳理周围社会关系时得知,一直关注红丝带学校的一位爱心人士和翠翠的大学校长熟稔,他欣然应允出面沟通。
障碍迎刃而解。翠翠清楚地记得,直到10月16日下午6点,学校终于开出请假条,同意她前往日内瓦。瑶瑶、涛涛、朋朋向各自大学请假亦有波折,都在郭小平的协调下得到了校方支持。
二
10月30日,临汾红丝带学校。
午后的阳光穿过梧桐树叶,打在郭小平瘦削的脸上。他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神态轻松:“到目前为止,日内瓦之行没有让4个娃的艾滋病感染者身份,在大学同学面前暴露,说明校方老师和领导们一直在为娃们保密,我非常感谢他们。”
16个孩子像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吹散到各个角落——15个进了不同的大学,1个去了南方学习刺绣。郭小平仍然时时牵挂着这些孩子。
这些孩子今年6月毕业离校前,郭小平创建了一个微信群,以便随时和他们沟通交流,掌握他们的动向,关注他们的生活、精神状态。郭小平最大的心病,是他们的敏感身份。如果被意外公开,将招致暴风骤雨般的歧视伤害。
这些孩子参加了当年防治艾滋病公益宣传片的演出,有的还参与拍摄过艾滋病题材的电影。郭小平担心他们一走进大学宿舍就被人认出。“实际情况比想象的好多了,目前娃们在学校状况不错,身份都没被同学识破。”
敏感的身份“标签”,如同随时起爆的炸弹,其实给孩子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考上北京一所大学的瑶瑶,经常梦见舍友一看见自己就集体离开、走在街上被路人斜着眼睛指指点点。“我特别怕同学在电视上看见我,知道我的情况。梦里的场景如果真实发生,我想那会儿应该是蹲在地上哭吧。”瑶瑶声称一直没有做好准备,去主动向同学说明自己的身份。
郭小平坦承,暴露是迟早的事,“他们吃的抗病毒药,是红丝带学校按时邮寄给他们的,每天要吃的。他们和同学一起住在宿舍里,吃药总会被注意到,被人问到吃的什么药,现在瞒着背着同学呢。久了一旦发现吃的抗艾药,别人会怨恨的——你干嘛要骗我!”
“这对娃们是很大的人生课题,这一关非过不可,感染者身份终究要向同学公开。具体何时公开,目前没有统一筹划,我给他们的一个原则是,你觉得与同学关系处理到位了,可以跟他们讲了,你就公开,不用再瞒。现在考虑的是什么场合什么时间点公开的问题。”
今年9月,郭小平原计划一个一个地送这些考上大学的孩子入学,后来放弃了。他不敢去。因为频频亮相荧屏,他早成了公众人物;现在又是移动互联时代,传播方式多样并且快捷,一去送就可能成为关注焦点,曝光孩子们的身份。
毕业的孩子中,最早的2004年就到了红丝带学校,最晚也是2008年来的。“他们很不容易,将来出身社会还面临很多事情,就业、恋爱、婚姻、生育等等,这些都是大问题,需要他们孤身奋战。”郭小平掏出烟盒,点燃一支烟。
10月24日自日内瓦归来后,翠翠把自己变得更忙了:除了用心扑在新媒体技术的专业上,课余还积极投身校园公益组织,有时也向同学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同宿舍的同学谈艾色变,甚至认为唾液都传染艾滋病。我故意说接触过艾滋病儿童,跟他们正常生活接触不会被感染,她们反而劝我远离,她们对感染者的接纳程度很低。”翠翠在微信上给我发来“大哭”的表情,“现在还不宜公开身份,我只求安安稳稳地度过。”


翠翠担心自己会被歧视。
三
翠翠饱受过被歧视的滋味。
她亲生父母均因为艾滋病离世,她在5个月大时被抱养。6岁上小学一年级时病发,发烧出疱疹,好转后去上学,她发现自己被孤立了,被安排到了教室最后面的右边角落里,没有同学和她玩。更糟糕的是,有一天养父突然接到校长指令——“你家女必须退学!”
翠翠只能回到家。连过去的玩伴也捂着嘴绕过她走,向她吐唾沫。 “直到现在,别人在旁边吐一口唾沫,我的心就感到冷冷的。”
2004年下半年,翠翠被送到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刚刚设立的“绿色港湾”。这是一个专门收治艾滋病病人的医疗病区,由闲置的非典隔离区改建而来,位于临汾校外一片田野当中,占地90亩。

翠翠刚来时,也是这样一个小女孩。
上世纪90年代,血液经济肆虐,很多卖血者和被输血者感染上艾滋病毒,因为没有“母婴阻断”,他们的孩子成为二代感染者,经过7至10年潜伏期而病发。2004年,山西全省90%的艾滋病感染者汇聚到这个病区。
此时,郭小平正在临汾传染病医院院长任上。生于农家的他,1984年中医学校毕业后,辗转于乡镇、县级医院,1995年调任临汾传染病医院副院长,1999年升任院长。
翠翠刚到病区时,高烧、呕吐、昏迷,医生多次下了病危通知书。郭小平坚持抢救,奇迹般地挽回了她的生命。
这只是郭小平当年收治的4名艾滋患儿中的一个。
这些孩子因艾滋病毒的侵害,大多没了母亲,有的甚至父母双亡。个个病体羸弱,性情孤僻,郁郁寡欢。当时国内尚无抗艾滋病毒药,他们的生命朝不保夕。
看着无辜的孩子,郭小平痛在心上。他有一天问翠翠有什么愿望,她说“想读书”,——被学校拒之门外是艾滋患儿共同面临的现实。
郭小平决定,在为孩子们治病的同时,在病区里设立简单的教室,开个小课堂。他把一间病房当作教室,找了一块黑板、四张桌子——一个简陋的“爱心小课堂”就成了。医护人员轮流义务担任老师,教孩子们认字、做算术,教材都是他们带的自家孩子的课本。
“建立爱心小课堂,让患病的孩子能在有生之年体验一下上学,过得快乐一点,这是当时的单纯想法。” 郭小平猛吸一口烟回忆说。他的身后挺立着红丝带学校的二层教学楼,爱心小课堂就是其雏形。
2005年,抗病毒药物来了,这种药据称能抑制艾滋病毒,增强免疫系统,只要按时服用,孩子们就能健康地活下去。一年后,病区的艾滋病患儿增加到8个,“爱心小课堂”不够用,郭小平添置课桌、椅子,依靠社会捐助,建起了“红丝带小学”。
“虽称学校,其实就是自己给自己起的名,没有手续,仅仅是一个称呼而已。”郭小平这样做的目的,只是让孩子们有一个上学的正式感,并无长远规划,因为当时抗病毒药物上市才1年,药效没显示出来,孩子们仍然生死未卜。
不管怎么样,总算把学校建起来了。那时防艾、治艾的宣传工作还未完全开展,大众谈“艾”色变,招老师就成了郭小平的心病。只要有教师资格证,愿意来的,他们统统招收。“我们待遇不好,又是这样的学校,没啥人愿意来。”郭小平记得,好不容易招来一位老师,第一次上课时竟戴着手套、口罩,穿着消毒外套,“比我进隔离病区还捂得严实,打心底里没有接受学生,怎么能教好我的娃们?”
怕这位老师的态度会伤害到孩子,郭小平只好让其离开。他记不清那些年换了多少老师,“没有任职超过半年的,最多时一周换了三位。”除了医院繁重的工作,郭小平还忙着给孩子们找老师。

郭小平将病房改建成教室,艰辛创办红丝带学校,为艾滋患儿们撑起一个家。
四
2010年,学校孩子增加到16人,抗艾药效果显著。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郭小平又有了一个心病:“红丝带小学”一直无办学资格。孩子们没学籍,也就拿不到毕业证,不能参加升学考试。
为此,郭小平开始考虑学校的转正问题。从这一年的下半年开始,他多方跑动,寻求合法审批,却毫无进展。
这是一个新事物,国内尚无创办这种特殊学校的先例,没人知道它该由哪个部门审批。到教育局,对方说还从来没有办过这样的学校;找卫生局,他们表示不具备办义务教育的资格;咨询民政局,他们回应:艾滋病儿童既不是残疾人也非聋哑人,这样的学校没法管。
转机悄然到来。2011年11月15日,世卫组织“抗击结核病和艾滋病亲善大使”、歌唱家彭丽媛来到学校看望孩子们,并和他们一起互动、同桌就餐。她的到访大大推进了学校的“转正”,经临汾市委市政府批准,“红丝带学校”在12月1日第24个世界艾滋病日正式挂牌。郭小平被任命为校长。
至此,这个全国唯一一所专门收治艾滋病患儿的学校有了合法身份,被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行列。给了正规学校的编制,加上防艾宣传的开展,老师的问题迎刃而解,20名教职员工到岗。
学校合法了,郭小平的心也大了——从初衷是让孩子能认字不当文盲,到期望他们上高中、考大学。2014年,红丝带学校16名初三学生在当地官方批准下,挂靠临汾市的中学继续读高中;今年他们全部参加高考,15人考上大学。
被问及13年来办学的艰难,郭小平笑了:“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难,一步一步,自然而然,拉拉扯扯娃们就大了。”
事实上,这多年来,郭小平和他的红丝带学校一直在艰难中坚持。
在红丝带学校,孩子们的吃、住、穿、医疗、学习等费用全免。在取得办学资格前,学校并无政府财政支持,运转一直靠临汾传染病医院出资和社会募捐熬过来。郭小平和老师们为节省开支,一直利用病区空地种菜自用。今年考上大学的15个孩子,家庭都贫困且大多数是孤儿,郭小平为筹措他们的学费和生活费,伤透了脑筋,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捐助150万元才成功纾困。
一个事实是,“红丝带学校”模式经常被外界质疑是“温室”和“圈养”。质疑者认为专门设立学校看似保护艾滋病儿童,实则加重了社会对艾滋病的恐惧和歧视,而且隔离教育不利于这些儿童的成长。
郭小平承认,这确实不是最好的办法,却是孩子们为数不多的现实选择,“如果没有这个学校,他们很可能面临死亡、无学可上。”
对艾滋病人来说,按时按量服药特别重要,如果不吃或者吃错可能产生耐药性,就得升级药物;药物的研发、生产又没有那么快,最后就会演变成无药可治。艾滋病患儿需要每天两次服药,而他们大多是孤儿或单亲家庭,谁来监督他们规范服药?在红丝带学校,孩子们的规范吃药被放在第一位,郭小平安排专门老师负责监督,“像生物钟一样到点必吃药。”
2015年10月底,郭小平辞去临汾市传染病医院院长职务,只担任红丝带学校校长。很多人疑惑不,郭小平回应:“换一个院长其他人也能做,但这个学校校长不是换一个就能做成的,因为这些娃认人,就认我这个人。我是用心在选择,娃们需要一个依靠的肩膀。”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陈雨露这样评价郭小平:“从医治人的身体,转向救助人的心灵,他投入更多的智慧和勇气。”
在红丝带学校老师朱然眼里,这两年来郭校长更忙了,特别是他和孩子们亮相央视《感动中国》、《朗读者》节目后,来学校的人一拨又一拨,他都要出面接待。10月29日,他牙病发作正在医院打点滴,一家公益基金会到校考察谈援助,“他拔掉针头赶过来,捂着腮帮子全程陪同。”

郭小平的办公室从来是敞开的,下了课的孩子经常进来粘他。这间屋子放置有一台冰箱,里面全是孩子们喜欢的各种吃食。
“这13年的坚持,我心里装的全是这些娃,为他们遮风挡雨,让他们和正常孩子一样接受正规教育,健康快乐成长,是我唯一的动力源泉。”郭小平说。
五
从临汾市区往东驱车十公里,拐进东里村的乡道,连片的耕地把道路夹在中间。不远处,红丝带学校在葱郁的树丛里若隐若现,一道灰色围墙将这里隔成了“孤岛”。
春天,芍药、玉兰盛放;夏天,梧桐花香满院。在艾滋病患儿们的心中,这里像一叶方舟:没有歧视,生活无忧。
46岁的李登军忙完孩子们的午饭,在我跟前一坐下来就哽咽:“我们学校像一个大家庭,郭校长就是大家长,操心着娃们的吃喝拉撒、学习教育。没有他就不会有娃们的今天。”
李登军带着8岁儿子,2008年从老家朔州来到红丝带学校,现在是学校食堂大师傅,儿子今年考上大学,“这是我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事,郭小平是我们父子的恩人。”
李登军夫妻都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儿子因母婴传播感染。2007年底妻子去世后,父子在整个村庄遭受孤立,“连亲叔叔一家都躲避我们。”儿子新学期一开学就被学校赶回了家。“看到娃这样被耽搁下去,我十分着急,想死的心都有了。”2008年4月5日,李登军找到郭小平,“当时就想让娃在这里上完小学就心满意足了,没想到他后来还能读完初中读高中,考上大学。”
儿子已长成一米七五高的大小伙儿,成了祖辈以来第一个大学生。李登军捧着儿子的录取通知书,“一晚上没睡着觉。”他自己也没想到,九年来一直留了下来,从养花工到食堂大师傅,干得特别有劲,“郭校长现在每月还给我发3000多块工资哩。”
学校门前的空地上,一群幼童嬉闹,笑声不断。“慢点跑,别摔着。”郭小平招呼着,不时抱抱这个搂搂那个。“大的一批走了,还得照顾好小的。现在学校还有23个娃,6个是这学期新来。小学一年级5个、三年级9个,初一9个。”李登军跑过来插话:“他经常跟我讲,千万别抠,不要节省生活费,一定给娃们吃好。他有时亲自下厨,还组织周末烧烤,改善娃们生活。”
就读北京一所大学的瑶瑶,一直馋着“郭伯伯”的炸鸡翅,怀念学校的烧烤,“尤其幸福的是,我们外出参加各种活动,你留在酒店,有事没事总会四处逛逛,找好吃好玩的,等我们回来再带我们去吃去玩”,她在写给郭小平的一封长信里说,“因为有你的陪伴,有你创造的环境,我们的童年完整,并不比别人的差,甚至比他们的好。”
翻看着瑶瑶的信,郭小平开始想念走出去的孩子。“娃娃们跟了我十几年,怎么能不想?!鸟儿长大了,总要往出飞,如果他们飞不动了,有什么问题或者受伤了,我还在这等着他们!”
这批孩子依然承担着沉重的心理负荷。对此,郭小平表示自责:“我过去对他们的教育,就是把学习搞好、上大学,注重分数,而没有进行必要的社会适应这种训练与规划。”
他对孩子们的未来十分清醒,“尽管社会越来越包容,但他们想要像普通人一样工作、生活,仍然不容易。这些大娃走后,我在教育心态、思路上发生了转变,不想让这批小的再接受枯燥教育,要走出去多接触社会,心理变得强大,心态更阳光,问题来了坦然坚强直面。另一个是从道德层面,更加强化自我规范,严格自律,树立‘到我为止,不再传给别人’的理念。”
郭小平正在策划系列活动,从明年起为孩子们尽可能多地创造条件接触社会。在学校课程设置上,每周六上午专门开设了科技知识课,介绍新科技动向,增强技能教育。
“建这个学校是无奈之举,”郭小平其实一直希望红丝带学校尽早关门,“这所学校没有了,就代表娃们可以到普通学校去上学,在没有歧视的环境里,他们未来还可以从事理想的职业,过上幸福的生活。”
(看看新闻Knews记者:邓全伦 编辑:余寒静)
推荐视频

剑网行动举报电话:12318(市文化执法总队)、021-64334547(市版权局)
Copyright © 2016 Kankanews.com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看东方(上海)传媒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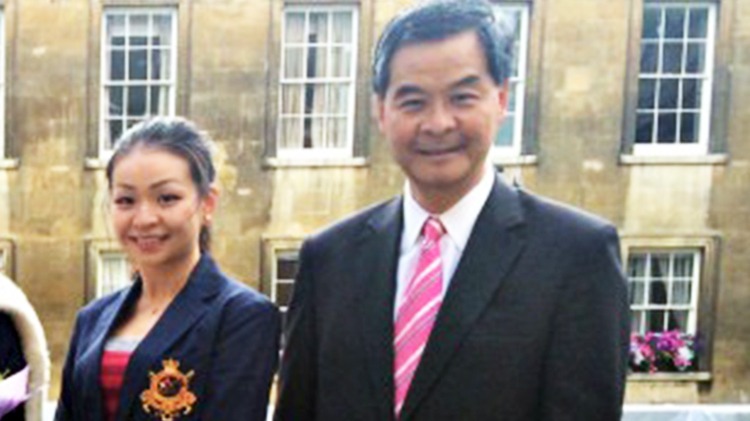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1114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1114号
全部评论
暂无评论,快来发表你的评论吧